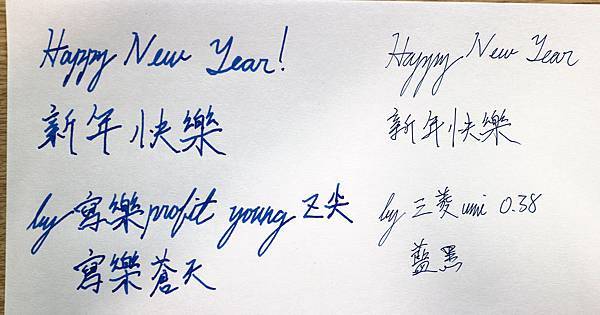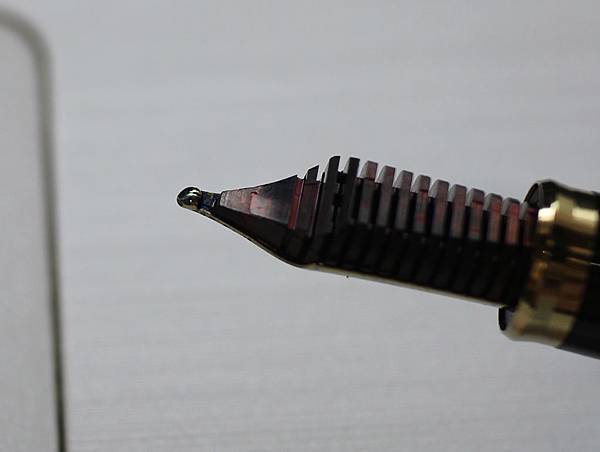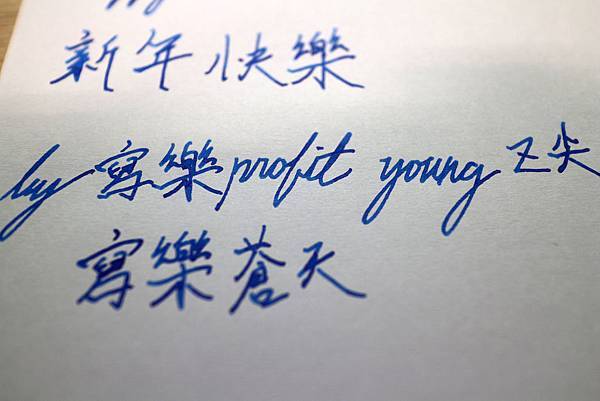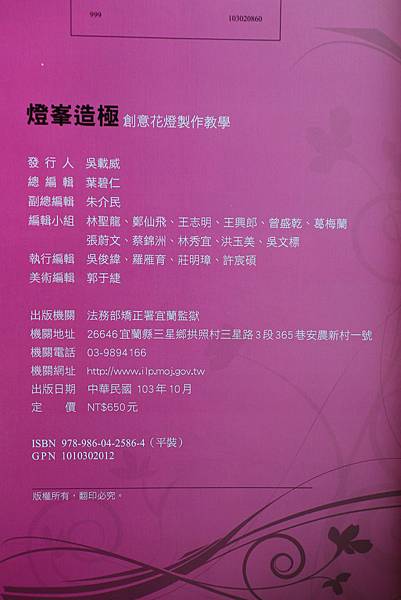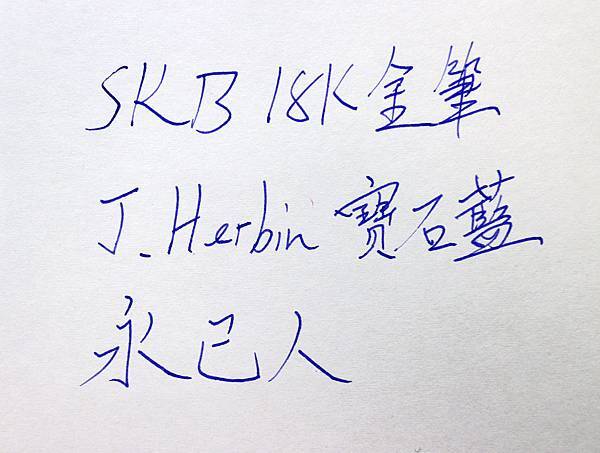金屬哀鳴下的白鼠
一九六三年,我們施家三兄弟在台北青島東路的軍法處看守所,已待了一年三個月,等待判決的日子,是難於用簡單的幾個字形容的,因此,一年後,我曾用十五首一輯的詩中的大部分來刻畫它!其中一首〈白鼠〉,以實驗室的白鼠,比喻我們在柵欄裡的生態,〈黑色金曜日〉,描寫禮拜五和禮拜二漆黑的凌晨,死囚從囚室被拉出來槍斃前,旁觀者、執法者、多線條、多觀點,所產生的震撼。〈金屬哀鳴〉,鐫刻獄卒手裡一大串巨大鑰匙的碰擊聲、開鎖聲,以及劃過鐵柵欄,那跳躍,奔騰如尖銳的彈頭破空擊向鐵柵欄,碎發的哀鳴,給人的恐懼和不安。這種聲音的恐怖,深沉在我的內心,久久無法消失。直到 蔣公仙逝之後,我在畫室裡為他佈置的靈堂,虔誠地禱告時,才把緊藏在我下意識裡可怕的金屬聲響,完全剝開、拋棄。雖然如此,如今,我在睡前,還要捏兩丸衛生紙塞住耳孔,以過濾、阻擋尖銳的聲響。
當你生活在一個絕對無法由你主宰的空間時,你會從逐漸學乖的體驗裡,形成某種樣品。由於人類異於其他生物,於是乎人類在多方思想、回憶,以適應生存的過程中,便自然地塑成了各種各樣的典型人格。
在我們尚未被判決的期間,已約略知道我們的命運。因為我們可以從起訴條款和當時所謂「判亂」案件採擷的多寡,來推知一、二。像我這種頂多也只判個五年的小兒科,便只好在吃了幾次猶大密告的小虧後,三緘其口,把自己砌下一層無形的厚繭和圍牆以保護自己。可是對於同樣被以二條三起訴,未被上面接納,終於以二條一項重新起訴的四弟施明德,原本沒什麼危險的,卻在改變條文後,一變而有殺身之險。這種無休無止的擔憂,分分秒秒以其有形的漩渦,把我捲進無邊無際的痛苦裡。
同是天涯淪落人
本文主角是跟我關在同一柵欄的一個外省人。我已忘記他的名字,雖然我們每個人總有一個阿拉伯數字的號碼,做為代號,但是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地方,因此人的名字被保留下來,這也許是我們享受到的德政之一吧!我所提到的這個人來自大陸,當他正以青年軍的身分,投筆從戎時,日本卻無條件投降了。之後,他隨軍轉進台灣,繼續保衛豎立萬丈光芒的自由火炬。也許是無親無故的孤寂,和倨傲的詩人性格,使他無法融為綠色裝大家庭的一員。以後被派到宜蘭某個中學去當教官。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隔著單調的大海,遙望那被籠罩在夕陽恐怖下的赤色大陸,因而昏了頭,有一天,他竟在台北火車站前,高唱某些口號,終以七條起訴,與我同關一牢房。
有些好事者,每見另一個生物被放進我們的籠子,總會過去撫慰同是天涯命苦者。除了偽幣製造者、走私犯、販毒犯等,能夠被調到籠外去執行雜役,以換得香菸、多吃幾塊豬肉、享受一些涼風的空間外,軍法處看守所可以說是乾淨的地方,它沒有司法看守所司空見慣的惡習陋規,這裡幾乎是人世間另一個經常發揮人類愛和人性光輝的地方。可是這也是一個磨碎高貴人格的磨石機,在這巨大的碾石機下,能不變形的,萬人之中,大約只有一、兩個。
每天吃過飯,我們在收起各人的碗筷,擦淨是散步的地板,也是吃飯的桌子、椅子,又是睡覺的床鋪,更也是讀書寫字的桌椅以後,都會不約而同地一個接一個在柵欄內,一圈又一圈地打轉。
開始參加這項打轉的生手,也即新客人,都會感到暈眩,因為這兒空間不大,兩、三面是鐵柵,一、兩面水泥牆,如果你不能把注意力移離於幾寸外的柵欄,那柵欄似乎會向你飛奔而來,迅速倒向你的身邊。這些無味已極的活動,使你深深意識到你是被參觀的實驗品,是某種生態學家、獵人和園主的傑出樣品。
這種打轉,在看守所裡,被公認是維持生命所須的重大條件:運動。可是,半坐半蹲在牆角裡邊的他,卻像一隻受驚過度的飛禽走獸,動也不動。我們只好在他身邊打轉。就像開始打轉一樣,收轉也是不約而同地,一個跟著一個逐漸離隊,由點線連成圓的圈圈崩潰了。人們在半個小時左右的溜腿中,重複了延續卑賤生命的重要課題,開始掙扎於在起訴時早已被決定的刑期宣判。
待在看守所裡的人,有十之六、七都已被起訴,十之二、三是判了刑,不敢上訴,以免惹怒命運之神,給你來個不知悛悔,怙惡不赦的結果,以靜待兩、三個月後,被分發到比較沒有肅殺、恐怖的執行單位,去接受消毒和隔離。最後還有兩種人:一種是未被起訴,在等起訴的人,這種人也大約可由他自白書、其他被告不利於自己的口供、和檢察訊問筆錄,略知自己未來的起訴條文和命運。由於起訴書很快就下來,所以這種人,便相對地少。最後一種人便是不服判決上訴,由十二年,變十五年,再變無期,然後死刑的確定者。而我待了一年五個月,跟三弟同被改為五條。判處我們幾乎知道是五年的徒刑後,被扣上有生以來第一次帶上的手銬,送往台東泰原(註:應指泰源監獄?)。在我們讀過的許多文學作品裡,每每看到外國跟我們同樣的情形被判者,在押送的途中,總會有人立正、脫帽以致意的情景;我們從台北到基隆所坐的軍用交通車隊,雖然沿途戒備森嚴,也有兩列憲兵機車隊開道護送,某些唐吉訶德型的囚犯,總把兩人合扣在一起的手,阿Q式地舉向窗口,顯示給好奇群眾看,以洩幽禁一、兩年,不見外人所積壓的鬱悶。
以鐵柵敲腦袋
有一天,我們在牢房打轉過後,每人各忙各的,誰也不想去打破那沉寂。
忽然,一陣奔過木頭地板的腳步聲,和頭蓋骨撞上鐵柵欄的悶響傳了過來。我跟同房,還有對面柵欄裡的人,幾乎同時抬頭,尋找,而且馬上看到用腦袋當鼓,藉鐵柵敲鼓的他,正站在鐵柵前發楞,在他確定沒有把脖子上的鼓給敲破以後,頗為懊惱似地,雙手緊緊抓住鐵柵,像拉單槓,又像鬥牛場的牛猛烈地撞了起來。
這種不是開玩笑的行為,已大大地違反了他一向大不為的常態。於是乎,他旁邊的人,和全柵欄的人幾乎同時地把他拉離鐵柵欄,我看到本來面向鐡柵欄,無法看到的表情,那是我這一生很難忘記的一張臉。從光頭流下的血,爬滿整佪臉龐,人靜靜地笑著,兩顆牙尖破裂而被擠成內V型的門牙,特別引起我的注意,使我聯想到,這些牙齒很有可能,也像他正在奔流著血的頭頂,是在夜深人靜時,沒咬斷鐵柵而斷裂的。
當他被看守我們的班長帶出去塗了紅藥水,再送進來後,他又恢復了那目不斜視、寧靜已極的痴呆狀態。
有些人挪過去勸慰他,得到的反應,一如我們看到他以來唯一的表情:一尊泥萻薩。
於是那些好事者,好像在敲了門沒得到回音之後,對他有了種種猜測。其中比較令我無法贊同的是說他在學孫臏,裝瘋賣傻,以換取改變條文,判他無罪,或者判了無罪,送他去政治犯的天堂——土城的生教所。過那沒有鐵柵欄,也不鎖門,可以打球,也可以帶著妻子、女友一塊兒上廁所排泄的日子。
可是,我總覺得這個人,像極了文學名著裡的悲劇人物。
我注意到他在接到起訴書後,一直沒有打開過。他幾乎是我所看到過的犯人中,東西最少的。沒有筆、沒有紙,沒有顯示他坐牢以前帶在身上的任何東西。他正像每個沒有親人接濟的人那樣,除了所裡分給他的一雙筷、一個鋁碗、一支湯匙、一條毯子,一套藍色囚衣(冬天,可以寫報告多要一條。但是他沒有寫過字,所以……)之外,只多了一套綠色內衣褲。因為他本來是個軍官,所以我無法肯定穿在他身上的內衣褲,,是不是從象徵著有限自由的外面穿進來的。
雖然我們房裡正像其他房裡那樣,總會有人買紙、筆和其他用品,甚至於把親友送來的水果、菜餚分給沒有親友的「同學」(我們都慣於使用這種稱謂來互稱)共享。但是,他好像從來沒有跟我們共享過,因此,好像連答辯書,也是我們同房裡的一個老先生替他寫的。這位老先生可能是從他的起訴書裡發現這個小同鄉,並在三問三不響後,基於同情心,根據起訴書草擬了一份答辯狀,並在他沒有答應,也沒有反對的情形下,送了出去。
因此,我把這個人列入絕望已極的人,應該不會太過分。
他很快被判了七年。七年在當時的行情,幾乎是僅次於五年的最低刑期(知情不報,不在此限)。正像我與三弟,和其他大多數的人那樣,不服上訴的有效期間,十天很快就過了。
這個對我來講仍然是沒有名字的他,以不同於一般人的方式,塑造了另一個生存的苦難典型。追溯其源,我乃豁然發現那是一種淒美已極的苦難之火。
他,這個用「不為」來追求「有為」的苦難同胞,雖然生活在我們身邊,卻以其「不為」隱遁其形象,使我們完全漠視其存在。
有一天,我們突然發現,他的肚子像氣球般愈脹愈大,他的小同鄉,那位乾瘦的老先生,嘴上喊著:班長、班長。一邊過去把開足水龍頭,猛灌自來水的他脫離水槽,一邊指著撒滿碎饅頭屑的地板說:
「報告班長,他剛吃下十幾個饅頭。」
「鬼叫什麼!?慢慢講。他怎麼會有十幾個饅頭?」班長隔著鐵柵欄問道。
「他把每天早上的饅頭,藏在他的帆布袋裡,這幾天他緊抱著它。」
這個開頭用鐵柵欄擊頭,沒自殺成的人,竟會想到用發霉變硬的十幾個饅頭和不知幾加侖的水,來結束一條卑微的生命。可是保護我們如此嚴密的獄政,卻救活了根本拒絕活下來的他。此後,他被關到別的房間,並跟我們一塊兒被遣送到台灣的東南方,台東的泰原。
台東泰原的一群
這個以「不為」成就「有為」的人,好樣在沒脹破肚子之後,稍稍正常過一陣子。聽說,他也寫過好些白話詩,不過由於跟我提起他的人,根本不關心白話詩,所以我無法知道他到底寫過些什麼,要不然他的詩裡,應該可以發現他的苦悶,並進而替他做做心理分析什麼的,以拯救這個作賤自己、粉碎自己,幾乎達到極度自虐狂的人。
在炎熱的台東泰原,我們住在一個頗具清涼詩意的清溪山莊。我與三弟、四弟在那裡度過了充滿悶熱陽光的三年多時間,早飯前和午睡後的半小時散步,使我們的生活竟也成為詩樣的記憶,閃耀在出獄後,東闖西奔,急欲重振被撕破的家園,而遲遲不可得的落魄時期。
他在泰原曾經穩定過一陣子,有時他也在放封時,跟著「仁監」二、三百個同學,繞牢房(全山莊分為仁、義兩個監獄。山莊蓋在斷崖之頂,佔地十幾甲,頗像一座山堡。)在高牆邊的長形方場,兜著圈,畫起圓。為了安全,我龜縮在我孤獨的硬殼裡。散步時,我絕少跟人結伴同行,以免被虎視眈眈的監獄,留下結群成黨的壞印象,也為同一個理由,我曾擺脫過他跑過來,跟我談詩的雅興。因為我怕背上黑鍋,怕被上面誤會我跟他的談話內容影響他在散步時高唱反動的口號。
就這樣,我失去了解他的機會。往後,他就在喊口號、關禁閉、用水泥磚撞擊他那傷痕斑駁的光頭頂的日子裡度過。
就像蠟燭即將燃盡那樣,一匹壯年的困獸,在無眠無日地揮霍他有限精力下,終於變成疲憊、無力、失神和虛腫。許久,他從我們的視界消失了。
仁慈的監獄官,派了一個癩痢的外役日夜照顧他,為了便於關顧這個糟蹋自己如此猛烈的苦命人,他們一齊被安置在兩坪大小的房間裡與監獄官室只隔著一條通道。
從此我再也看不到他,雖然放封時,全監的同學都會經過他的小房間,但是好像沒有人注意過他。我也自覺身處是非之地,應該潔身自好,明哲保身,於是我乃埋頭創造詩、畫、小說、電影分鏡頭腳本和翻譯,並完成施明正推拿術。
回憶面壁五年的生活歷程,我覺得頭一、二年和最後一年的日子,最為緩慢而痛苦,第三和第四個年頭,由於習慣了,刻板的日子便機械式地飛馳而去。
就在這麼缺少變化而寧靜的日子裡,牢房的通道口,起了一陣罕有的騷動。開頭,我們都想不到是他製造的騷亂,因為自從他由我們的視界消失後,已有好長一段時間,全監獄聽不到他的騷動和消息。由送早餐的外役耳語中,我知道,他成功了。他死了。
他的死,怎麼能算是成功?可是自我看到他以來,他的行為,好像都集中在尋找死路上;不斷地試、力行,而終於完成他的弘願。也許死的魅力,一直深深地誘惑著他;可是我不了解,要找死,不是應該留在監獄外?在那裡,你要怎麼死,不是頂容易的?然後,我又想到我們中國人,是一個絕不流行自殺的民族。因此,他的尋死,說不定是在喊了不應該喊的口號之後,落了網,才慢慢形成的。或者他的死,也是三島由紀夫式的一種行動美學之追求;他死於三島由紀夫之前好幾年,因此不能說是他模仿了三島由紀夫。寫到這裡,我深切地後悔沒有跟他做過任何溝通,以了解他尋死的原意,和他對詩、對人生、對人類、對世界,究竟有過怎樣的看法。何況被他垂顧的,僅有寫詩的我而已。
聽說,他的死法,非常離奇,他在癩痢頭起床外出洗臉刷牙時,脫掉沒褲帶的藍色囚褲,用褲管套在磨子上,結在常人肚臍那麼高的鐵門把手中,如蹲如坐,雙腿伸直,屁股離地幾寸,執著而堅毅地把自己吊死。
——原載於一九八零年十二月《台灣文藝》第七十期